细雨版(Helen朗读)
一九七五年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晚上九点十分
晚安。
(“赛斯晚安。”)
口授:在对等人物及意识的家族之间有一个关联。
就像你与你的兄弟或姊妹是属于同一个物质的家庭,所以,一般而言,你与你的对等人物是同一个心灵意识团体的一部分。可是,要记得,这些心灵团体是像意识仿佛流入之自然的形成物。你自己的兴趣、愿望及能力并没被你在一个既定心灵家族里的会员资格所预先决定。
举例来说,你并不因为你是苏马利才喜爱创造性地游戏。反之,因为你喜爱创造性地游戏,所以你才加入苏马利集团。那么,意识的集团不可以与,好比说,占星术的十二宫相比。
且用苏马利来作个例子,可以有过度热切、深思熟虑或根本是沉郁的苏马利,他们还没学会优雅的带着喜悦的去用他们的创造力。然而,对那能力喜悦的利用会是他们的意图。以你们的说法,在历史的某些特定时期里,不同的家族可能会占有优势。
不过,心灵的团体部分重迭在具体的及国家的团体上。举例来说,苏马利是极端独立的,而按照常规,你不会发现他们生在独裁的国家。当他们真的如此出现时,他们的工作也许会引燃一个火花,而带求改变,但他们很少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创造性对这样一个社会是非常具威胁性的。
可是,苏马利是实际的,在于他们将创造性的展望带入物质实相,并试着据以生活。他们是创始者,但他们很少试着去保存组织,即使是那些他们觉得相当有益的。他们天生就不是犯法者。以最严格的说法,他们也非改革者,然而,他们游戏性的工作确实常常导致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改革。他们的确热衷艺术,但也是以最广的说法,比如说,他们试着去让生活成为一种“艺术”。他们曾是大部分文明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最少出现在中世纪(公元四七六年到一四五〇年)。他们常常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之前全体动员。举例来说,其它人可能由苏马利的工作而建造出社会性的结构,但苏马利本身虽然觉得高兴,通常却不能够觉得与结构性的团体有任何直觉性的归属感。
在前边的小节里赛斯引入了意识的家族(灵魂社团)这一新概念,在之后的几个小节里会慢慢地展开对此话题更深入的探讨。意识的家族被分为以下的九大类:
1、祖里(Zu’-li)2、苏马菲(Su-ma’fi)3、米尔伍梅特(Mil’-u-met)
4、依尔达(Il’-da)5、格拉玛大(Gra-ma’-da)6、佛德(Vold)
7、度莫(Tu’-mold)8、柏莱汀(Bor-le’-dim最接近苏马利的一族)
9、苏马利(Su-mar’-i)
在这里我们需要认知到,中文对于“家族”这一名词的认知是含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我个人觉得这个名词翻译是不贴切的。这里我们用“灵魂社团”,比“意识家族”更贴近我们的文化理念认知。
一个更大的“意识角色”分化与分流出像树状的意识束,同时对不同的面向展开同时性的探索,形成多层次平衡性的体验和认知。在追求个人性、个体力量与群体性、群体发育中有一个认知理念上的过渡。
就好像每个学校都有各种兴趣社团、健身社、古典文学社、诗歌社、野外生存社、学生社、玄学社、心理学社、爱心社、助教社…… 一到八年级的学生们入学后按照自己不同的兴趣,跟随某一个社团或随着成长更换社团。社团中都是相同理念与兴趣的同学们。一般双胞胎会选择在同一个社团中,但这并非是一种必然,而是多数规律。而一个家庭里的多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会依据自己的性别与爱好选择不同的社团。
虽然每个社团都同时对各个年龄段各个年级的同学开放,但是几乎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成熟度的孩子们,集中在与自己年龄相适合的社团中。虽然任何社团对性别都一视同仁,但性情的天性让不同社团中男女比例形成了自然的偏重。
比如“苏马利”社团培育着高度心智成熟的高年级临近毕业的助教们,它们对一身腱子肉或拿着开山刀去闯荡野山林已经没有兴趣,对小女生的浪漫或背诵唐诗三百首也过了那个年龄。它们会去帮助与辅导低年级的同学,把自己童年时走过的弯路总结成经验、给出自己的忠告,但是不会去替这些学弟学妹们答写考卷或抄写作业。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前,它们会特别地活跃。
虽然它们带来的影响力可以改变世界的走向,但是也会妨碍其它社团的自我挫折被体验到。比如小男生在疯狂地锻炼腱子肉或小女生看着言情剧、憧憬着浪漫的童话王子这种心理成长的过程是需要被经历的、是需要被尊重的。你不能上来就说:去刷卷子吧,去读名著丰富阅历吧!那就打破了体验的平衡性与自由意识的多样性。
当下这个版本的地球其主体文明有着自己的必然轨迹。作为苏马利,你不能去改变本版本地球自身的必然趋势,因为每个版本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因此带着渴望体验这一实相的角色们去破釜沉舟。你可以独善其身或大声疾呼,然后自己选择自己要经历的地球版本,跳线到不同的平行世界里的那个地球上去。但是这样的跳线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你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渡,就好像1到10之间有着无数个1.1、1.2、1.3一样。渐变的过程中,你会失去所有跟你不同频的角色们——它们在你的实相中离去或死去了。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做不到孤家寡人,那你会最终留在一个最大公约数里。
(九点三十八分暂停。)
可是,在意识的家族及身体上的特征之间并没有相关性。许多苏马利选择在春天出生(注一),但并非所有在春天出生的人都是苏马利,而此地并没有一般的定则可以适用。他们也对某些种族有一种喜好,但再次的,没有特定的规则适用。比如说,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西班牙人及较少数的法国人是苏马利——虽然他们出现在所有的种族里。
一般而言,美国一向并非一个苏马利的国家,而北欧国家或英国也不是。心灵上来说,苏马利非常精心的安排自己作为“少数人”——比如说,在一个民主政治里,所以他们可以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情况里致力于他们的艺术。他们对政府并没兴趣,然而,就彼而言,他们的确依赖政府。在那个架构里,他们有自恃的倾向。他们被承认的艺术能力可能居于主宰地位或只是微乎其微的。
苏马利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倾向。他们不是斗士,通常他们也不会倡导以暴力推翻政府或习俗。他们相信自然发生的改变之创造性。
无论如何,因为他们很少是随俗者,所以他们常常是文化的地下组织之一部分。一个苏马利非常不喜欢作任何大型商业组织的一个成员,尤其是如果那工作涉及了习惯性或令人厌倦的例行工作的话。他们不喜欢在生产线上。他们喜欢玩味细节——或把它们用在创造性的目的上。他们为了那个理由,常常从一个工作或职业换到另一个。
(九点五十五分。)
如果你开始审察你自己的天性,而直觉的感觉你是一个苏马利的话,那么,你应该找一个你可以用你发明才能的位置。举例来说,苏马利很喜欢理论数学,但却会是个凄惨的记帐员。在艺术界,毕加索是一个苏马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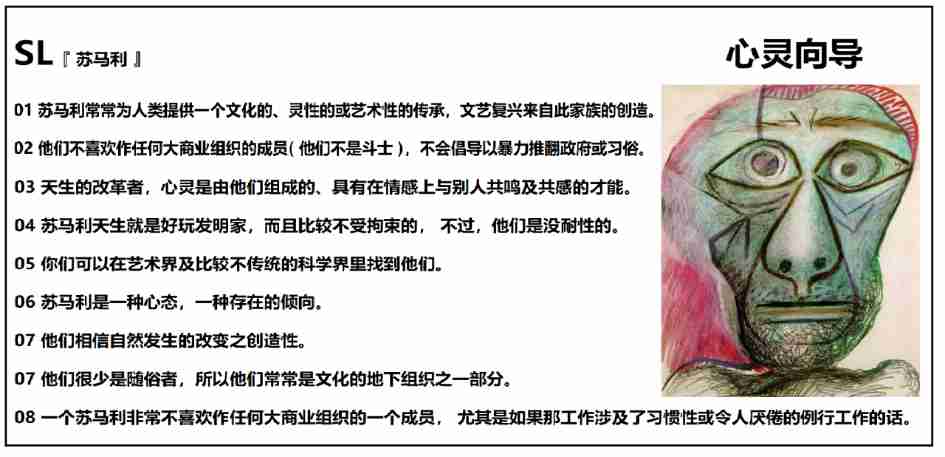
一般来说,苏马利们选择投胎的国度有着较为懒散的文化氛围,多选择生发的春季白羊或金牛座当令的人物角色作为自己的频率身份。它们不太喜欢快节奏、高竞争或文化压制的国度、人文社会。对物质、名誉、财富没有多大兴趣。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学生”,但不怎么学也不会落后于平均线。
当然季节和国家不是绝对的特征,因为有些角色是十分难得的。利用这些角色的身份时,难免会在某些国家与季节出生。不过它们中的多数之后会选择移民到一个相对轻松的生活环境中,因为它们已经厌倦了因利益而引发的生命功课。它们不甘于把自己当成资本的奴才与玩具,或流水线上的“机器”,它们不在乎是否生育或传统意义上迂腐的爱国主义与儒孝理念。对于“幼稚”的政客和长辈,它们内心中充满慈悲的怜悯,而非崇敬的盲从。它们偶尔随口说出的“金句”可以让身边的朋友顺利地从半生的迷茫中走出。
它们普遍喜欢“道”、“上德”层面的东西,可以轻松地理解本质的奥义,但对繁琐、单调、机械性的运作匮乏耐心。它们乐于为世间带来创造性的开拓,引领一个新的纪元,因此少被大众主流赏识。那些超前的理念少被当代科学所理解,更无法被“大众”认同,在死后多年,其成就才会慢慢地被重视。对于传统守旧的父母来说,这样的孩子实在不是自己拿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体制性社会的“栋梁”。
(九点五十七分。)
请等我们一会儿……
演艺圈内的人许多是苏马利。你很少在政界找到他们。他们通常不是历史学家。
(停顿良久。)他们很少在有组织的宗教内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因为他们自力更生的天性,你可以发现他们身为农夫,直觉的耕作土地。他们平均分布在两性里。不过,在你们的社会里,在男人中的苏马利特质直到最近以前都多少为人所蔑视。
你可以休息一下。
苏马利们多数很明白自己是演员,也乐衷于当个演员,用艺术的夸张表现力传递出一些令人警醒的启迪。但是它们普遍对政治或宗教团体没有兴趣,对于用这些幼稚的手段去引导民众前进早就脱敏。它们很少去研究历史或传递所谓的编年史,因为深知时空的多元同时性,任何线性的历史观与未来预测都只是第六阶佛德Vold们玩的“洞”见类把戏——这种童年期的探索它们已经不感兴趣。相比之下它们宁愿去耕耘,伺候土地,培育花草蔬果。
这样毫无进取心与“担当”的苏马利“人”被我们习惯地叫“玛丽苏”,在女性角色中更容易以温婉的品性被人们接纳。但男性被社会更多地期许成“进取型”的性格特质,这种中庸的状态就很不符合激烈的社会预期,并严重地影响着家庭中的物质生活品质。苏马利之间最好形成婚姻,不然连生育理念、财富的竞争手段、为人处世的利益抉择都成为家庭内部战争的问题。两个意识频率相差太大的人无法在同一个意识频率实相中共同滞留得太久,除非一方已经达成全然的通透,不会被低频意识形态的习气熏染扭曲,有全然无挂的智慧对境应付各种是非、争执与拉扯。
注:
(玛丽苏的故事——是那些最年轻、最聪明角色们的传奇历险故事。主角总是年纪轻轻就拥有逆天天赋与跨维度觉知力,轻松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这些角色通常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技能,从能力到智慧基本还有很高的幸运值。这类角色很容易被多名异性同时青睐,而自身处于无辜的被动开挂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拯救了时代,达成不可能的人文,最后连死后都会被众人铭记。这样的角色的存在严重地打破了多数底层读者渴望公平竞争的基础期许,被多数人鄙夷。这个名词“玛丽苏”被广泛地与那些格外幸运——幸运得不真实的角色联系在一起。)
不过话说回来了,普通人眼中的“平等竞争”是基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此生的公平。但一个才历经千年的灵魂小白与一个已经历经万劫的深紫金光灵魂谈公平竞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啊!
十点一分。
我写下两个问题给赛斯,并且读给珍听:
一、就算赛斯对时间的观念是对的:转世的人格是否通常透过种种不同的意识家族去经验其同时性的人生,或他比较可能在所有的那些人生里维持对一个这种家族的“忠诚”?在今晚课开始时,赛斯曾说,一般而言对等人物是同一个心灵家族的一部分,但我想知道是否转世的人格也是如此。
时间的同时性与流动性是一个相对可以互换的概念。就好像电视剧拍摄的过程中它确实有流动性,而拍摄完的四十八集电视剧成为了同时性的存在。而观看它们的时候,不管是按顺序还是跳跃着看重点,流动性的时间又被启动了。这个在房间里看电视的你被监控录制下来,你的一天是流动性的;而晚上来查看监控的保安看这些画面时是同时的。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关注不同素材的影视作品——英雄主义的、浪漫爱情的、惊悚灾难的、科幻鬼怪的、人与自然的……成年后就不再会看动画片了吗?未必。但小孩子看纪录片时确实觉得无趣。意识可以向下兼容,但没有经历过的经历确实很难被理解与形成感受共鸣,也无法诱发必要的觉受思考。
对等人物之所以能对等并形成彼此交叉对立的人生体验,因为意识觉知的发展程度基本类似。你无法与一个六岁的孩子一起读完名著后深入地探讨人生哲学——类似的心智成熟度带来心灵的碰撞。转世的概念与同时性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感。因为前者有先后的排序,而后者则是并列存在的关系。我理解这里涉及从多层不同次元上看待每一层次元时的特有独立视角关系——彼此相对都是同时的,而自身则表现出线性的特质。比如你看完一部电影后,你从那个影片中的时间线上跳出,然后选另一部电影来观看,这个动作是线性的时间概念;但你选的下一部电影,其发生的时间可以早于或晚于之前的这部影片,或是同时代的故事。你选择的题材可以是雷同的,因为你就好这一种类;或差异的,因为你想调剂一下自己的感受。
二、动物及其它生物或“无生”物与对等人物及意识家族之概念有何关联?
我们都知道珍是被认知的苏马利,而赛斯是其更高完型中的一个阶段性身份。在早期赛斯承认它还有一个片段是一条狗,即动物体的存在,并提及过有时为了意识上的放松,会去选择在某个星球上当几百年的树木。引申的思考:地球作为一个活着的大石头,它的意识觉知要被归纳到哪个意识家族中呢?它也应该有自己的对等人物吧?那或许是另一个星球,或许是某个不起眼的微尘颗粒,体验着全然对等的生灭体验。
(在听我讨论第二个问题一、两分钟之后,珍说她有了一个答案,或至少是个部分的答案。她的答案应该是由赛斯那儿来的,虽然是由她说出来。正当她开始说话时,她被一阵沉重的敲门声打断!人是敲在二楼公共门厅的大门上,然后就在我们两间公寓的门上。一个女性的声音大叫珍的名字。我们等着,但那坚持的嘈杂穿透了风声,正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会带来的:今晚课的结束。当我打开了门,我面对着一个面貌姣好却非常心慌的女人,我暂且称她为芭芭拉。她大约四十出头,身边摆着一个很贵的衣箱。
(“你们没在等我吗?赛斯告诉我你们会……”,
(当然,珍和我都没预期我们这来自外州的不速之客。在这儿我要说,后来珍在《心灵的政治》的第十八章里更详细的谈这整件事。在这儿且让我说,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非常害怕她自己的精力。因为那个恐惧,她衍生出某些问题,足够严重到让她不能从事她有关法律上的工作。
(芭芭拉坚称她需要帮助,但就如在珍和我曾碰到过的其它例子里,她是如此贯注在她的苦恼上,以至于我们无法破解它;至少无法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赛斯最后也透过来了——珍在那类状况里几乎从不容许发生的事——但也无能为力。芭芭拉就是无法理解她在创造她自己的实相。
(在令人困恼的两小时之后,我把她送到一间汽车旅馆去,当我回来时,我告诉珍,芭芭拉已经作了一个决定:明天她要搭飞机飞过半个美国,去看另一个必然能帮助她的通灵者。)
你无法有效地帮助一头尾巴上点燃了鞭炮、在恐惧中失去了理智而狂奔着的牤牛安静下来。虽然旁观者可以清晰地知道,那鞭炮压根儿没有杀伤力,而整件事情不过是小孩的恶作剧。但牤牛持续感受到被如影随形的未知伤害是真实不虚的。
(注一:我们也许无法将赛斯指定为那一个具体的种族,但他却是一个苏马利:“不瞒你说,还真是一个非常高阶的苏马利呢!”他在第五九八节里谈苏马利意识家族的第一节里很幽默的告诉我们。一个月之后,他对他自己的实相提供了更多的洞见。那么,由第六〇一节里:
(“正如我的名字基本上没什么重要,所以,苏马利这名字本身也没什么重要。但那些名字指明了一种用到某种界线之独立而独特的意识。
(“你们的(苏马利)意识就是那样一种的意识,而我的也是一样,只是我的界线远不如你们那样的局限,而我不把它们认作是界线,却当作是方向,而对我自己的认识必须在其内生长。这同样也适用于苏马利族。换言之,现在对你们说话的不是一个未分化的意识,却是一个了解它自己身份本质的意识。
(“它是一个个人的意识。可是,在我对我身份的认知及你对你实相的认知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你懂吗?”
(我说我懂。
(“重要的是,以那种说法,我并不比你们更不个人化,而再以同样的说法,苏马利也是个别的,并且到那个程度,是个人的。你是苏马利的一部分,以简单的说法,你有某些特质,正如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成员可能有某些特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