嗔恨如刀自刨心,怨妒如蛇侵入髓。
一念无明爱生恨,念念相随何时脱。
本来兴旺的鸟群,在归巢期被罗网捉去很多低飞的幼鸟,母鸟救子心切也随后落网。劫难过后,群落萎靡,成年雌鸟损失过半。所幸大批雌性幼鸟因飞得慢,晚到了几天躲过了这一灾殃。
鸟群里有那聪明的,它们记起有回巢早的看见了人类,却没有给后续队伍发出预警,于是把无法向人类发泄的愤恨转移去霸凌我们的女主,不听她的辩解,满树林地追着她啄咬踢拽。这样闹腾了很多时日。
群落数量的骤减,让今年的食物显得格外充足,小鸟们长得很快,发情季也来得格外早。大量的雄鸟在初夏归巢时失去了伴侣,此刻卖力地炫耀着自己的舞蹈、歌喉与翎羽,相互为建造鸟巢的小树枝打架。而雌鸟中大多数是刚进入成熟期的幼鸟,在它们眼里,去年的老阿姨、前年的老太婆们根本就没有和自己争夺交配权的资格。
我们的女主“鸯儿”看着那些和自己去年同样稚嫩的小家伙们,对她们的跃跃欲试觉得可笑。自己现在是群落里最美的成年雌鸟,这大批的光棍们即使跪舔我的脚趾、每日殷勤讨好,都要看我是否有心情搭理他们。这些个雄鸟一个个精虫上脑,满脑子就是那点事,我可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擦亮眼睛,找个帅气的、有领导力的、脑子好的、无不良习惯的、壮实的、对我好的、能逗我开心的、会哄着我的,最重要的是会打窝的。对了,还不能太窝囊。
脑子里想着勾画着,不由得痴痴笑了。林间的雌鸟少但光棍多,竞争确实很激烈。鸯儿遇到了几个求偶者,不是猴急地想要搞事情,就是呆瓜,还有那傻大个儿,一点儿都不会讨自己欢心,她都果断拒绝了——她可不想让那些精英误以为自己身边有人了。
迁徙季又开始了,她才发现一个自己忽略了的大问题:
雄鸟确实多,但符合自己条件的却百不足一,而且雄壮聪敏的根本就不参加求偶的闹剧。几乎所有的雌鸟择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那些今年新长大被自己看不上的小丫头们,她们一点儿不懂得什么叫矜持,好几个围绕着群队里优秀的雄鸟,倒追甚至倒贴。
自己现在要不随便找个被所有人挑剩下的,要不只能找身残志坚或脑残体壮的。营地里还没启程的像点儿样的雄鸟中,还有些自己有伴侣还到处找小姑娘的,要不就是把伴侣祸害散了,此刻准备再祸害别人的。
到底是闭着眼随便将就一个,还是再等等呢?
冬去春来,鸯儿随种群又独自飞回了夏季的林地。这次她觉得不等了,只要有谁向自己表示好感,那就是他了。这一年的林间非常热闹,又有一大群幼鸟成年了。鸯儿看着那些羽毛鲜亮、体型婀娜的小丫头们,三五成群地叽叽喳喳,心里有些复杂:她们的妈妈和自己同龄,可自己却还是单身。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是那些健硕的雄鸟却像敬重长辈般地礼待自己。不管是同龄的还是年轻的雄鸟,他们都只盯着那些小丫头看。那些翎羽凋落连飞都飞不动的老家伙,自己又真心看不上。
鸯儿决定今年要主动出击,自己看上的,就全力争取。她自己筑巢,她捕捉虫子给雄鸟吃,她把自己的羽毛收拾得焕然一新。可是她发现,即使这样,那些被自己“照顾”的雄鸟,还是不能忠诚地对待自己,他们看见那些小贱货就好像馋猫看见了鱼。鸯儿为了能保持那脆弱的关系,而选择了一次次的隐忍。她不想孤独地飞过万里江山,她不想再次产下没有受精的蛋。
飞行的路上,突然鸟群惊恐四散,地面上有枪声传来。伴飞的那雄鸟第一时间就采取了闪避的姿态,并且护住了同飞不远处的另一只孤独的雌鸟。鸯儿,却没有改变自己的飞行轨迹,她好像对此浑然不觉。然后她感到胸膛被重击而撕裂,那痛楚很短暂。然后它继续飞行,而一团血肉模糊的什么东西直坠地面。
“我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尘世剧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入轮回!”在无尽的昏暗中,女人愤怒地嘶吼着。
“如你所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无尽的黑暗,永恒般地持续着没有时日的光阴,涛涛冥河浪哗啦啦的,犹如白噪音持续不断。没用多久,女人的所有情绪都被这虚无消耗殆尽。她可是一遍遍地回想自己能想起的一切,可就连这回忆也有品味到无味的时候。永恒的无聊就犹如食心的蛆虫,无时无刻不在啃咬着她的灵魂。窒息的死寂让她哭嚎呐喊,渴望被聆听,有个互动,可四周都是这哭喊嚎叫的声音——就是它们构成了冥河的涛声。
这时她才发现,虽然在轮回中、在尘世里有种种的不如意,但至少那一段段的经历,让自己感到自己是活着的,一幕幕变换的身份与角色是那么有趣。如此不死不灭地在这里比自己能想到的任何痛苦还要痛苦。这是对厌世者无声的刑罚。
而判自己入这无间地狱的不是所谓的判官,而是自己!

“我受够了,我想离开这里。但我不想再做女人了!”
“如你所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
“大头、大头,走啦,别看了!”有伙伴叫着自己。
站在箱子上的男人岁数不大,此刻正努力保持脚下的平衡,好让自己的视线可以透过高墙看到院内练舞的女孩们。他痴迷于那领舞的女孩,她的一颦一笑都让自己心头一荡。女孩子们知道有坏小子偷窥,但乐于戏弄这些傻小子。那小眼神、小动作,妩媚得勾魂。
大头姓鸳,从小在王府里长大,父母就是王府的家奴。他没什么志向,也没学过书文,从小练了些把式,想长大后当个护院,娶个院子里上岁数后的丫头,人生就美满了。
自从他看上了领舞的鸯儿,就好像丢了魂似的,总来趴墙头,让同伴们笑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配不上院子里的那些姑娘,可是抑制不住渴望亲近呵护鸯儿姑娘的心思。在别人眼中,那鸯儿姑娘是俏皮活泼的,但自己总觉得她眼神深处隐藏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幽怨与无奈。他渴望把鸯儿姑娘拥在怀里说:不怕,有我呢,我带你离开这里,打破你我宿命的枷锁。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鸯儿姑娘最终接受了自己的爱,并在一个风花雪月的浪漫之夜以身相许珠胎暗结,鲜血染红了身下的衣裙。

月余后,鸯儿悄悄来找大头哥,神色慌张,她说月信未至,恐是……
府里规矩大,丫头大了肚子,是要受乱棍之苦,然后被撵出府门的。
俩人商量再三,想要私奔却无银两。打小就在府上讨生活,对院门外的世界如何运作几乎一无所知,更不会什么农耕商贸手艺可糊口养娃。再加上身上本就不多的银钱,这些日子都买了衣裙胭脂,出了府门第二天上哪里讨饭都不知道。最后决定,设法让王爷当孩子爹。当然实在的好处是不能让他占了去的。一再推敲后,大头哥去药店搞些“曼陀罗花粉末”当蒙汗药,然后找机会碰瓷王爷——全院子里只有他能扛起这件事来。
俩人的计划可谓漏洞百出,但王爷却好像纯得要命,居然没有怀疑,照单全收了。还许诺要是鸯儿能顺利产下世子,就许她名分地位。之后侧妃几次使坏,好在有惊无险。临盆产子那天,王爷叫大管事通知院子里的几个小厮准备车马,最迟后天要送一名女眷去燕山脚下的庄园。随行之人中就有鸳大头。
大头担心着正在生死关上徘徊的鸯儿,本想找个由头过两天去小院里看她,可这要是被派遣出远门,往返一趟少说半月,到时候鸯儿会不会怨恨自己不闻不问啊。再三和管事推脱,但管事说随行人众是王爷亲定的,没得商量。大头隐约总觉得这里有事,心底忐忑。
眼看到了第三天,就要出发时,大头一狠心,故意崴了脚,想要借故留在王府里。没想到管事铁了心让自己必须随行,哪怕坐在女眷的马车上,也要跟着走,说在路上养上两天也就没事了。大头实在拗不过,只好上车随行,结果发现车厢里的人正是自己日夜惦念的鸯儿和一个内院里的嬷嬷,只是鸯儿此刻脸色苍白昏睡不醒。
马车在官路上晃荡了几天,一切都很顺利。其间鸯儿醒过一次,但又很快昏睡了过去。随行的老妈子每天给昏睡中的鸯儿喂下葫芦里熬制好的汤药,说是产后补气血用的。老嬷嬷为人倒也和善,没有嫌弃自己一个大男人同车随行。只是她言辞闪烁,说话时眼光游移,让人感觉怪怪的,大头倒也没有深究,想是空间局促,相视对坐总是难免尴尬。
这两天大头其实都没能睡好,他一方面担心鸯儿的身体,怕她半夜醒来有什么需要,嬷嬷睡熟了没能照顾到;另一方面他总觉得心里惶恐忐忑,好像被虎狼在暗处环视般有莫名的压迫感。他自嘲多虑:两辆大车走的是官道,还有王府的随从徽章,怎么也不会有事的。
同车的嬷嬷说:“看你的脚伤也好得差不多了,可眼睛都熬黑了,过两天到了地方,你怎么做事啊,你也喝口这补气血的药汤吧。出门时大夫人慈悲,让多带了些,怕路上耽搁了不够用,眼看就要到地方了,放着也是多余,你就饮了去补补身子吧。”
大头再三推脱,还是拗不过嬷嬷的一片好心,喝下一碗药汁,只觉腹内温暖入口甘甜有点微辣,不多时昏昏然果然有困意袭来,就瞌睡了过去。梦中自己和鸯儿在田野上自由地奔跑,鸯儿追不上自己,干脆蹲下耍脾气,自己无奈只好回头去哄她开心。
突然感觉背后剧痛钻心,梦中看见一只大熊从背后偷袭了自己,它的利爪撕裂了自己的皮肉,鲜血从伤口处泉涌而出。
梦境碎裂,自己猛然回到车厢内,想要挣扎可全身瘫软无力。
四周都是血腥味。然后突然就不痛了,身子一松,轻飘地能动了!
自己一跃下车,发现这是一处野湖岸边,同车的嬷嬷被人扶上另一辆马车,府内三个护从换上了黑衣服,两个人搬运着软泥般的鸯儿,给她脚踝处绑上大石。鸯儿好像醒了,在央求着什么。另一个黑衣人把自己的肉身从马车上拉下来,丢在芦苇荡边,然后用大锤猛砸马车。
大头愤然冲过去想救鸯儿,可是自己犹如在幻梦中般,轻易穿透了对方的身体。不管自己怎么挥舞拳头、怎么喊叫,他们都毫无感触。大头突然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好像已经经历过一次,或几次,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混乱地出现……那些人都走后,野湖边重新平静了下来。不多时蛙鸣鸟叫又开始回荡,好像刚才的事只是一梦,从未发生过。只是芦苇荡旁自己的尸体与碎裂的马车提醒着自己:这不是梦。
突然背后有人叫自己,那声音好熟悉,居然是鸯儿——她不是被沉湖了吗?!

大头心道:难道这一切都是梦?也好,如此相伴倒也如意。
这些年俩人偷摸约会做贼一般,如此可光明正大不被打扰地相厮守,实属难得。
起初还深恐美梦短暂好梦易醒,可是两人多虑了——从那一刻起,时间恒定不动,天永远是灰蒙蒙的,四周有走不出去的迷雾屏障。
……
日子久了,这耳鬓厮磨的天长地久让大头和鸯儿深感惶恐。
这不再是一场美梦,而是无法醒来的梦魇。大头认定是那汤药有极强的催眠能力,怪不得之前鸯儿会在马车上昏睡不醒,一定是那嬷嬷在汤药里动了手脚。如此昏睡下去一定是凶多吉少。可是他俩尝试了各种方法,也走不出这迷雾丛林、离不开这片水域,就算掐大腿、咬舌头也无法醒来。
直到有一天,突然天光大亮,从光束中有个人形走出来,说:
“是时候回魂醒来了,不要错过这一机会。”可是鸯儿犹豫再三也不愿或不敢随大头步入那光中。
大头想:不知道如此耽搁下去,后续会发生什么,但俩人都被困在这梦境里,肯定是无法自救的,之前我们能想到尝试的方法都证明无法脱困。如果我能先醒来,在现实里救她醒来,可能成功的机会远比俩人都被困在此处要大许多。
于是大头让鸯儿别怕,在这里等他,他会设法从外边唤醒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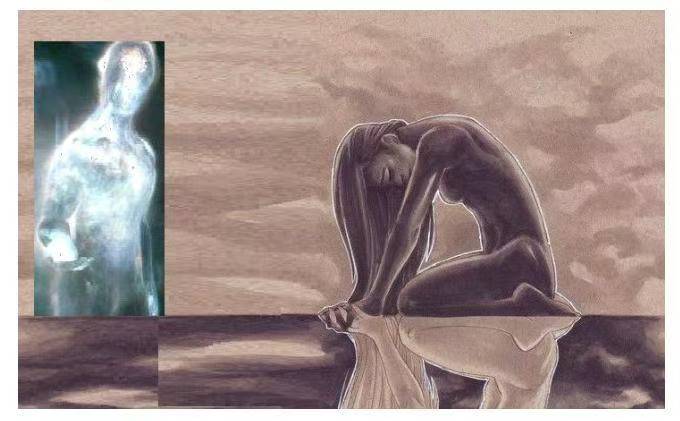
涛涛冥河水,冲刷着暗无天日的河床。顽石般沉寂的自我意识,犹如宿醉后被渴醒想喝水的人,清醒与朦胧、梦境与现实,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两个不同的记忆混乱地交缠在一起,头脑中有个念头:要去救鸯儿,要设法改变这一宿命的轨迹。
我要怎么做呢?无力感、迷茫感,涌上心头。他(她)觉得一切悲剧幕后的黑手是王爷:杀手如此行为,两人被安排去山庄,肯定都是王爷的主意。如果我是王爷,我就能救下鸯儿,让她在王府里幸福地过完此生……
……
军帐中,将军挣扎着醒来。
下体的疼痛让最强力的“麻沸散”都无法长久地镇痛。将军挣扎着起身,看见自己裆部被包裹得犹如大粽子。自己刚才的挣扎,让鲜血渗出殷红了纱布,疼痛犹如巨锤,让自己又昏迷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