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随军神父的卢思卡,跟着圣女军团在共和国境内几次转战。虽然都是农民、灾民、逃兵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但却奇迹般地所向披靡,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残酷战斗。就是粮草问题一直是个困扰,好在都是穷苦人出身,饿肚子也习惯了。
卢思卡作为神父,活动还是相对自由的。他在各个部队间来回走动,安抚人心,稳定大家的情绪,借机寻找自己的儿子泰美斯和玛依的女儿斯佩斯。
军队中都在盛传:要面对的敌军不是别人,就是几年前叛变的伯爵与他的军队。
卢思卡想:如果可能,或许自己可以劝双方和解。其实这些圣女军没有具体的政治野心与目的,只想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过日子。毕竟都是老百姓出身,在哪里都是过日子,没有谁真的关心谁是王或皇、这片土地是共和还是帝国。百姓的日子就是耕作、生活、纳税、婚丧嫁娶这些琐碎,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之间在相互争斗蛋糕的切法,而彼此血拼的方式却是让百姓成为炮灰,焦土千里,白骨遍野。
就在大家都在庆幸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准备过好日子时,前线传来消息:圣女在军阵前与叛变的伯爵相认后叛变,之后神秘失踪。
共和军投降的部队突然哗变,圣女军原地解散,顽抗者将被剿灭。驰骋了一年多、浩浩荡荡辉煌一时的圣女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犹如滩涂上的沙堡,消散无形。
卢思卡脱下自己穿了半生的黑袍,换上农夫的衣服——共和国境内的宗教与自己的体系不一样,他的身份不被这里认可。
解散后,他继续在各地走访寻找自己儿女的下落。同时利用每天的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学总结成书,并起名为《另一个世界》。
在暮年时,他辗转回到家乡,在老友胡撒的教堂里度过晚年,并完成自己的著作。每周他都会去原来玛依和孩子们居住的小屋收拾一番,总盼着有那么一天,孩子们就奇迹般地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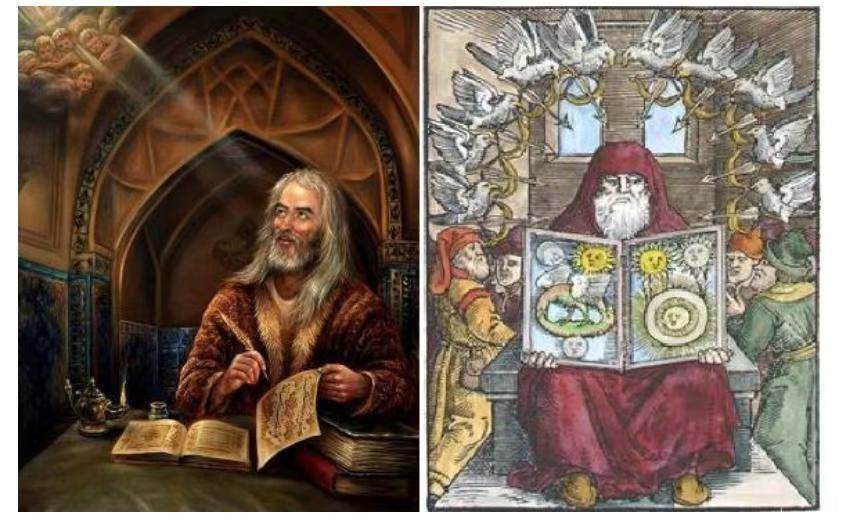
归
卢思卡觉得自己大限将至,独自来到山坡上,在玛依的“身边”躺下。夜里,看着满天的繁星,他也不想要什么坟墓,身体归还给大地与生灵们就好了。夜里的风很凉,他开始还觉得冷,但慢慢地不觉得了,甚至有些暖和,甚至是热。
等了很久,天都大亮了,自己却没有死;等到中午还是没有死。卢思卡很奇怪,坐起身,突然觉得全身很轻快,犹如少年时的感觉,老年的沉重感荡然无存,骨头的酸痛也没有了。
他看向山野、溪流、草、流云……都好鲜艳、好美丽、好清晰啊,视野清晰极了!
卢思卡非常纳闷:这是怎么了?难道冻了一夜自己就返老还童了?没准是命不该绝,先回教堂吧。
刚想到这里,自己就出现在教堂里。他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在做梦吗?卢思卡想找胡撒说说自己的遭遇,可是他对自己视若无睹,听而不闻。他想要拍这个老伙计的肩膀,自己的手从他的身体上直接滑过了,好像胡撒只是一个虚影一般。对着胡撒大声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只是忙活着自己的事。
卢思卡发现自己可以穿过关闭的门窗,甚至墙壁都不过是被光影虚拟出来的。有些人的头顶上有一条烟雾状的、高亮的线绳通往天际,那线绳似有还无,有两根手指粗细。但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光辉傍身,多数人是没有的。他尝试着去触碰胡撒头顶的这能量流,结果自己能感觉到他在想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很有意思。
卢思卡突然想:我是怎么回到教堂的?刚才我还躺在玛依身边呢!这样一想,自己又瞬间回到了那山岗之上。令人惊骇的是,他居然看见自己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地上!
卢思卡完全懵了:我是在做梦吗?我在这里?我在那里?哪个是我?
卢思卡小心地走到躺着的卢思卡跟前去碰触它,结果那个躺着的只是一个虚影,自己的手从它的身体里毫无阻碍地穿过。
这时,他听到茅草屋里有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很熟悉,居然是玛依和孩子们!卢思卡快步来到房间里,果然他们仨就在里边,仿佛正常地在生活,年龄与相貌都还是自己记忆里最后的那个定格。
突然,眼前的时间开始倒带般回放:孩子越来越小,玛依越来越年轻。然后就是场景被切换又切换:自己回到了修道院……
玛依在努力地生孩子……自己被困居在抄经阁,研究着密书……
自己回到了毕业前……回到了开始的那个家……回到了一片灰亮但空虚的空间内……
这是哪里?四周什么都没有,望不到头的虚空包裹着自己。
眼前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高亮的点,犹如暗夜中的太阳。卢思卡想要知道那是什么,心念一动,那个亮点在急速地朝自己迎面扑了过来。

四象
“你好啊,阿尼!不记得我了吗?”
那个光球传递出意识,回响在自己的脑海里。
那个光球传递出意识,回响在自己的脑海里。阿尼?谁是阿尼?我在哪儿?光影中走出一个人影来,那人影很亮。卢思卡尝试着眯起眼睛看:是一个女人,那面庞……是、是……玛依,是玛依!
“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哪里啊?你还好吗?”
玛依慢慢地走近,笑得很温馨:“我都好,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有些时日了呢。”“你们?谁是你们?还有谁?”
玛依背后又走出了一个女人的光影,居然是斯佩斯!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找了你很多年,也等了你们很多年。
玛依,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还把孩子们弄丢了。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你们可见到泰美斯了吗?”玛依微笑着说:“他就在你这里啊。这些年他一直伴随着你、守护着你呢!”突然,卢思卡感觉自己体内好像有一股力量,一股男性的、阳刚的、坚毅的力量在凝聚,然后从自己的身型中硬生生地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两个自己——分离出来的身型正是自己找寻了多年的儿子泰美斯。
卢思卡彻底蒙了:“你,你怎么会在我的身体里?你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啊?你怎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我找了你多少年,又等了你多少年吗?”泰美斯看着卢思卡说:“自从我命丧沙场,我就回家来了。
可是你看不见我,也听不到我。很多次我在梦里和你说话,但你醒后也就忘记了。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帮助你化解了很多你都没能意识到的危机,并成为了你活下来的坚强的勇气与力量。”
玛依说:“你终于完成了你的人生使命,你写完了那本《另一个世界》,恭喜你。”卢思卡看向玛依,又是一惊——那脸庞是玛依,可身型却是一个男人!
“你的身体!”卢思卡惊愕地、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违和的缝合体。慢慢地,玛依的脸也消失了,变成了五官模糊、毫无辨识感的一片。
紧接着,她身后的斯佩斯也是如此,儿子也是如此,它们的脸孔都雾化了,失去了轮廓感。
卢思卡吓得倒退了一步:“你们到底是谁?”
这时那个大光球突然说话了:“阿尼,它是阿尼姆啊,你的对等意识面向啊!斯佩斯,是它阳性面中分离出来的阴性面。
而你身边的泰美斯,则是你阴性面中分离出来的阳性面,看看你自己吧!”卢思卡低头看着自己,自己竟然不再是男性的身体,而是一个女性的身姿,也是一团光雾般的存在。这,这,这是我吗?
我是什么?我是怎么了?这一切都是怎么了?
大光球说道:“这解释起来非常地复杂,很快你就会知道,并回忆起全部。记住,等你醒来后,来休养大厅找我们,我们在那里等着你。不见不散啊!”说完这些,四周的光影开始扭曲、溃散,出现了一条旋转着的光道。卢思卡感觉自己被吸引、拉长、扭曲,然后从原地被拉扯到了那光道里,一阵眩晕……
再醒来,仿佛一切都是梦一样,自己躺在一个石台上。一时脑海里还很混乱,她想起了自己好像刚刚躺在这石台上,只是刚刚。

自己是阿尼,不,自己是被负心汉庇佑斯毒死的圣女蓬皮亚;
不,自己是神父卢思卡;不,自己是阿尼。休养大厅,海边,吵架,阿尼姆,普鲁沙……
我好像还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年代有过短暂的一个童年。那个童年被照顾得很好,只是自己没有多少印象。那个时代好像有能在天上飞的马车,人们的衣服也都很特别,建筑都是像水晶般的高塔……
定稳心神后,阿尼跳下石台,走出意识环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教堂般辉宏的大厅,两排侍从在讴歌着当中的主神。那三面神笑眯眯地看着阿尼:

“你回来啦,我的孩子!你做得很好,为我带来了很多收获。
我知道你遇到了不少坎坷,为什么不再求助于我的力量帮你轻松化解呢?我能做到的远比你能想到的还多。”阿尼看着它,不卑不亢地说:“谢谢你,我找到了我想要理解的爱与被爱,也懂得了经历人生的意义和这经历的价值。
我觉得一切的历经都有其寓意,而每个人都应该直面自己的人生课题,利用自己的心智去化解自己的问题。利用外求获得捷径,快速地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确实很省力,但那不会带来自我的成长,只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感谢你,在我情绪低沉、充满愤恨的时候,给我上了这样生动的一课。让我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尽管这在很多时候会因为利益的摇摆而各自在得失间形成记恨。
恨只是因为自己想要的没能得到,愤是心中无法平复的情绪在左右着自己的理智。现在的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与满足。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的在意是如何局限了自我的成长。”那大神说:“很高兴,我的孩子,你获得了你需要的,而我获得了我需要的。你看,我是一个最公平的神,我的交易从来都是平等的。如果你沉醉在贪婪里,那我就收获你的生命;
如果你享受着生命的教诲,我就收获你的喜悦。
去吧,回到你来的地方,享受你余下的旅途。如果有一天,你感到苦闷、愤恨、无助、绝望,就再来找我,我很乐意随时给你你的所求。当然,一切都有它的对等代价,这就是平衡的法则。”两边的护卫们,又开始吟唱对大神的礼赞与歌颂。阿尼听着这圣歌,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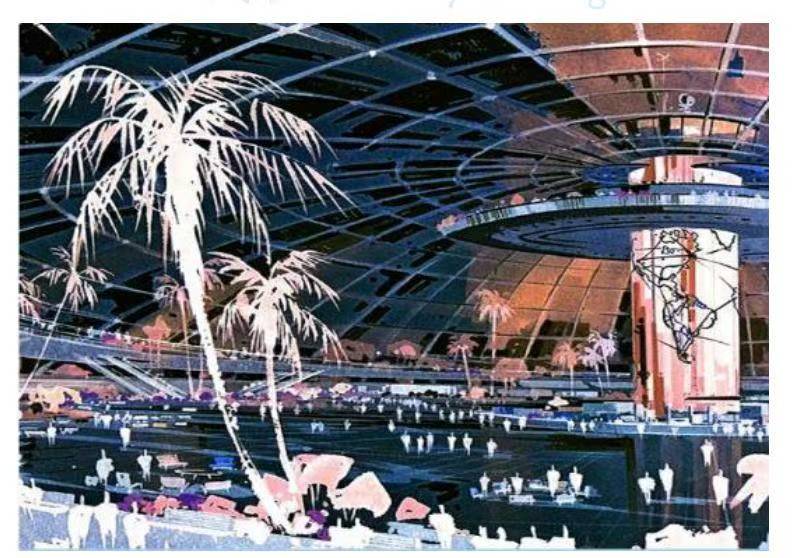
回到中心广场上,一切还是那样熟悉。自己上次和阿尼姆闹脾气,气冲冲地从休养大厅跑出来,也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这个呆子为什么不追过来劝自己、道个歉呢!不过想想,如果当时他真的追过来道歉,自己也还是会端架子把他骂跑的。
阿尼突然想起普鲁沙说的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我们现在是四个不同意识面向的意识个体了:我自己、阿尼姆,还有我们各自衍生出来的阳中之阴斯佩斯(希望)与阴中之阳泰美斯(平衡)。它们此刻应该都在休养大厅等着自己呢!
阿尼此刻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一种久违的能量感充斥与鼓舞着自己,头脑清明而敏锐,脚步轻快犹如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