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的张府门前很是热闹,佃户们赶着大车来交地租,送来很多粮钱家畜。
往年此时的张员外一定会亲自逐笔过账——他可不是个马虎人,甚至可以说有些斤斤计较;可今日此时的张员外却在内堂的客厅,而且门窗紧闭,与一位方外的高人密谈着什么。
这个张员外年近四十,还膝下无子,娶小也有两年多了,就是不见动静。两房女人这几年不停地喝各种药汤汁,可是却都泥牛入海,打了水漂。
这高人据说是路过此地的散仙,今天一早敲门说是来报喜。
一见到张员外开口就说集福得报,是送儿子来的。
员外看此人才二十出头,手拿算命幡,背着个破包,衣着普通,以为又是个江湖卖药的,吩咐家丁给他几个铜板送客。
可这人却开口直断,说中了好几件张府内隐秘的私事,张员外才半信半疑地把他请进内室详谈。
这半仙说他游走四方,今早看见张府内紫气云聚,这是大吉之兆;但这紫气游移聚散并不稳定,看来好事还在五五之间。
他愿免费帮张员外促成此事,事成后张员外看着打赏就好。
若不能,分文不取。
张员外好奇问他:“要怎么配合呢?”
半仙说:“我要在府内住上七天,在家宅各处布置阵法,聚拢祥瑞之气,同时日日在内宅祈福祝祷。而七日后,员外要亲自去趟五岳之首的东震泰山,到金顶之上礼拜吃斋七日,等回来后好事可成。”张员外心中算计:七日后,今年的地租也就收完了,在家中横竖无事,去趟泰山金顶祈福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反正对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只是这一去要两个月才能回家,到时都快入冬了。
张员外问方士:“你这七日祈福,和我去泰山祈福,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吗?”方士说:“你带上两位夫人去泰山,至于谁有缘给你生下大胖小子,就看两人的气运了。我这里不用特别准备什么,给我一间内院的偏房住下,方便我这几日做法就好。还有,这是一个紫金的通灵铜铃,这些日子请员外务必挂在腰间,好让全园的福气都可以凝聚在您一人身上。”
七日后,张员外携原配夫人去泰山祈福,而二房却因前夜承欢时感了风寒,高烧不起,无法随行。那祈福的方士说他懂医术,可以祛病救灾,愿意在此多逗留两天,为二房治病。
而员外必须要在秋分日出之时赶到泰山金顶之上,过了那个时辰,这运势就变了。
员外有些犹豫,想等几天带上二房同去,可原配夫人一再催促张员外动身,怕耽误了时辰,于是一众家丁丫鬟簇拥着员外,前后十辆大车起行去往泰山,家里留下不到三成人手,打理家务,看门护院,照顾二房起居。
两个月后,张员外回府时,二房出来迎接,羞答答地递给员外一封信,是那个方士留下的。方士在信中说,他为二房治疗风寒之时,意外发现她已有喜在身,二房本就体弱,所以没敢用虎狼之药,为了保胎治病,前后拖了一个半月才治愈病根。但因二房没能随行去泰山祈福,恐祥瑞不足,所以这个孩子或许会早产。过几个月他会回来保这母子平安,顺利产子后请员外按照约定打赏。
事情传到正房耳里,结果就是好大的一阵风波,各种小话在院子里四处风传。张员外一怒之下处置了几个碎嘴的,才把事情平息下去。二房的受孕证明他还是够男人的,不孕的问题都是正房不争气。这一点绝对不容质疑。
数月后,临盆之日,方士果然如期而来。张员外佩服此人算无一漏。方士说这个孩子名字中要带泰字,方能平安成年。
这是员外此生唯一的独子,需好生珍惜。员外送他金银答谢,他送员外固本保元的丹丸二十四枚作为回礼——员外只要每月吃一粒,就能身轻体健;若与正房分食,一年内或许还能添个女儿。
一年后,张府出丧——员外与大夫人双双死在春宵帐中。据说张员外这一年,勇猛异常,入秋前经常尿血。二夫人这一年哺乳不能承欢,而大夫人急于受孕拼死配合,导致多次月事崩漏大出血。官府认定这是纵欲而亡,受了好处,也就不四处声张了。全部家产由张泰易继承。
自打老爷夫人诡异暴毙后,后院经常闹鬼夜间哭啼。二姨奶请回了一年前的方士入住后院内宅,常年镇鬼护宅。
张泰易慢慢长大。懂事后,妈妈与家人只叫他泰易,多年后张府也改名叫泰府,引来外人种种议论。泰易在成长的过程中,义父教了他很多行走江湖的术法,还经常给他讲故事。
他慢慢地知道了义父的家乡离此地有百里,他是母亲的同乡,和母亲只差两岁,是从小的玩伴。
又过了十年寒暑,母亲过完三十大寿没多久,懵懂的泰易偶然撞见义父与母亲在房中讲法,两人姿态古怪,神情慌张。
之后泰易被送回母亲老家的一处道观,精学天地德行,若不学成不可下山。
此处道观,名为问心观。十二岁的泰易就这样成为那不大的道观里年龄最小、但辈分仅次于掌门道长的小师叔,道号太易。

泰易在道观里长到十八岁。这期间家里隔三差五地送来银两,道观中看这个小师叔就是财神转世,一众后入门的小道士,整天溜须拍马为了骗些银钱,好去集市里打牙祭。当家道长也不太管束他,只要不捅下天大的娄子,多半都睁一眼闭一眼地放纵。
这一朝的皇帝注重老庄之道,厌弃佛教,所以十里八村的人都来道观祈福。泰易本就长得俊朗,一身气质与道观中的那些土包子更是无法同日而语,自然引得很多妙龄香客脸红心跳、小鹿乱撞。在观里修行的这几年里,泰易的本事道理没懂多少,青年的女修却都被他撩拨了个遍。
冠礼将近,他本以为这就是自己回家的时候了,可是收到来信,妈妈说会带人返乡祭祖,并在本地祠堂给他行冠礼。这让他很郁闷,他本想走出这山观去外面看看,可是又有些怯懦。
冠礼前后,他听家里随来的丫鬟婆子碎嘴,说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公子,所以不让他回家。他为此事质问母亲,却被义父斥责无礼,母亲也不置可否。第二天母亲就带家丁们回去了,临走前还是那句话:学成之前不得下山返家。
泰易去问掌门道长,什么标准才算是学成,老道苦笑摇头,说他答不出,因为他还不敢说自己已经开悟了呢。
泰易决定把这个道观搅和得不能容他,好把自己赶回家去。
结果半年内道观里、周围几处村镇,就有好几个黄花大闺女大了肚子。
女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幸运的唯一,她们想着以身相许私定终生后就是花轿红烛,等来等去反而出现了妊娠呕吐,被家人师父臭骂。各家转念想母凭子贵,嫁入豪门也不算亏。等打到泰易姥姥家要说法时,才知道门口都要排大队了。本就不大的地方,这下可炸了锅了,各家的闺女被人前人后地指指点点。各家的长辈也是气急败坏,反而泰易跟没事人似的躲了起来。道观里也找他,母家也找他,那些大肚子的姑娘们也找他——他人间蒸发了。
其实就在风头日紧时,泰易的义父半夜来找过他,泰易准备好被斥责一顿,被领回家去,但义父却只是跟他喝酒赏月,说些自己听得半懂不懂的人生道理。然后只记得晕的乎地醉了。那一晚的梦好长,自己好像坐船、坐车,经历了很多事情。等酒醒时已经天光大亮,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一个陌生的老道士在照顾他。
泰易想回家,想回原来的那个道观。老道士说去那里要半个月的舟马路途,需要一大笔盘缠,现在身子还虚,真要想回去,也要等过了冬启程才好。这说话间就要大雪封山了,此时出发,没有马匹恐怕活着走到县城都难。而道观里并没有马车或马匹可用,年前恐怕也不会有香客上山进香的。
泰易明白了,自己这辈子恐怕也别想回家了。而自己长大的那个道观,现在被自己搞得也一准不会再接纳收容自己,回去指不定还要面对各方面多少压力呢。看来自己此生注定要是个道士了,这世俗上的事已经与自己无缘了。
老道士说:“送你入山的人只留下了两个月的香火钱,休息几天后,你要在观里做事,不然可没有余粮养闲人的。”泰易并不知道,在他走后,原先的问心观被骂得一塌糊涂。
女修们都没脸待下去了,渐渐地没人再来上香。春去秋来,道士们纷纷散去了。其实这些年来道观都是依靠泰易家的鼎力资助维持着门面,泰易失踪后,这一助力也就断供了。
深秋后,问心观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新任的道长,道号“地上人”。据说他是三年前加入进来的,他之前有个师父,叫太一真人。那太一真人门下有三个徒弟,分别叫“天下人、人中仁、地上人。”而这个地上人最不成器,又不服气天下人得了师父的衣钵,一气之下离开了原先的道观,就来此挂靠了。
深秋的清晨格外寒冷,婴儿的啼哭犀利持续,地上真人起床寻声来到大殿,看见地上有一个包袱,包裹蠕动,襁褓中有一男童。男童手上有一个廉价的首饰。道观为了积德,夜不闭户,若有路人夜间赶路错过了宿头,可在大殿中忍一宿,不会被寒风禽兽伤害。这孩子看来刚断奶就被特意遗弃在此了。
泰易后来在道学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可是刚过花甲,就被一场普通的风寒断送了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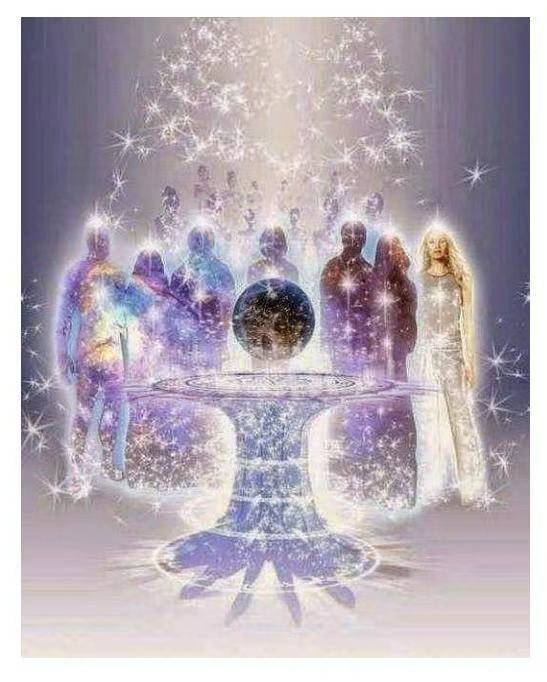
普鲁沙回魂回来,在眩晕感中恢复着。
史匹擦问:“可有进展?”
普鲁沙苦笑说:“看来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薄情郎。进入角色后,一路下来,身不由己。我想如果我能早点儿醒悟,不去祸害她,多半她就不会羞愧难当,正常地结婚生子,人生轨迹就能转变了。等我缓缓,要想个办法再尝试一下。”史匹擦说:“那在你冠礼前后,加入一场濒死体验,让你能有机会解离出来,好破幻醒悟,如何?”普鲁沙说:“好吧,那再尝试一遍,或许我可以不把她裹挟入这场乱局,不让她触发走投无路的状况。”光影旋换,一个男婴哇哇落地。一年后张员外和大夫人病逝,泰易在妈妈三十岁生日后被送回老家修仙。成年冠礼前的一夜,他因醉酒跌落池塘,五月水寒,溺水后高烧三天不退,差点儿死了。病愈醒后心性大变,判若两人,不但出口成章,还小小年纪自具大师风骨。冠礼后他不求归回母家,反而恳请母亲给予资助,让他能去游历名山,拜师问道。
泰易走后不到半年,乡间瘟疫四起,很多人离乡逃难,导致十室九空,问心观从此没落。深秋后,老道长在大殿内捡到一个弃婴。其母已不见踪迹。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此事与我无关,是我想多了。看来我要换个方法才能干预此事的发展方向。”

光影旋换,太一真人门下的小徒弟地上人拜别师门,下山游历,寻找落脚的道观,来到了问心观,成为道观中的外门执事。后来观中的一个混世魔王搞出天大的风波,道观声名狼藉,没落了。他和两个残疾的老道士无处可去,留在观里自己成了新任道长。深秋之夜他辗转难眠,于是去院子里扫落叶,夜色下看见一年轻女子瘫坐在大殿中。想要上前询问,看她好像正在哺乳,就没冒失打扰。过了一会儿那姑娘哭着跑出大殿,地上留下一个包裹。
地上道长快步上前叫住姑娘,告诉她落下包裹了。女孩一惊,犹豫纠结胆怯地否认,然后又恳请道长慈悲照顾好那小家伙,说自己实在无力抚养其成年。道长说如今道观落寞清苦,也无女修,真的无力抚养幼儿。
女人和道长说,自己要孤身远行寻夫,路途上匪患连绵,带着孩子母子都凶多吉少,求道长帮助照顾小孩,短则三日长不过七天,迎归丈夫后一起来道观答谢,带走孩子。
道长问清她的性命家宅,与其约定照顾幼儿三日。但后来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道长去那个村子住址查访,邻居说女子命苦,父亲好赌败光家业,许久不见,不知生死。她一年前黄花闺女大了肚子,惹来各种非议,数月前她没叫产婆,自己生养下来。没死就算命大,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儿来的奶水给孩子吃,身子虚得干不了活计,拖累着月科里的婴儿每日哭啼,白天晚上的不能睡觉。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这次至少知道了她的角色名叫艾萌芯,家住在道观往西十里外的吴家村,是多年前逃难来的外乡人。父亲好赌,家徒四壁,她留下孩子是去寻夫。恐怕弃子时还没有寻死的念头。看来我要从更源头处下手,才能转变这一命运。”光影旋换,农家院内一女婴出生,家境贫寒,父亲对其很不待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骂她赔钱。月信初至,十二岁就被许配给村头的莽夫,而莽夫答应帮她家里忙活三年秋收。
没承想转年就开始大旱,连续半年不下雨,全村纷纷逃荒,从此她随莽夫来到数百里外的吴家村落脚,并有孕在身。年仅十四岁的她,被迫大着肚子还下地做活。她家是外来户,开垦的田地在离村很远的山窝处,早产加难产发生在农田里,莽汉干着急却没有丝毫主意。
产后发生大出血,女人临死前告诉男人,希望孩子日后心明眼亮。男人抱着孩子回了村。村里的老人问男人姓什么,男人说从小家人只叫自己憨蛋,不记得姓氏。
村里老人说:孩子生在艾草田里,女人希望她心明眼亮,就叫艾萌芯吧。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我以为当她妈,总能影响她的童年与情感方向,与她形成信念连接,但这看来行不通。好在了解到的细节越来越多了,接下来需要知道搞大她肚子的男人是谁,或许这能阻止她寻短见。”
